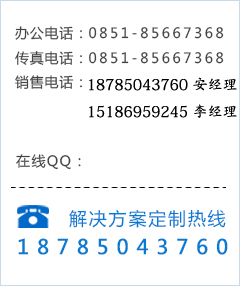多重困境污泥處理亟待體制創(chuàng)新
?
在日本大阪,舞洲污泥處理中心由政府投資建設,日常運營完全依靠居民的污水管理費。在一些地方,污泥焚燒制磚之后,除了補貼,政府優(yōu)先購買用于市政建設。在另一家污泥處理工廠,甚至負責人就是市長,政府部門協(xié)作極少“打架”。
2016年4月18日,一輛大巴停在了日本大阪市舞洲人工島上的一座“童話城堡”前。
69歲的講解員吉田先生穿著藍色工裝,將一臉錯愕的中國參觀者迎進了會議室。這座有著藍色煙囪、橙色外墻的“城堡”,是他們計劃參觀的舞洲污泥處理中心。每天,大阪市12座污水處理廠產(chǎn)生的約四千噸污泥(含水量98%),通過地下管道流入這里,經(jīng)過脫水、干燥、熔融,最后變成25噸無害的黑色顆粒狀熔渣。
自2007年建成以來,舞洲污泥處理中心已接待參觀者近兩萬人次。吉田很享受“污泥”與“城堡”的巨大反差在參觀者臉上造成的表情變化。
不過這一次,面對“中國青年豐田環(huán)境保護資助行動”研修團(以下簡稱研修團)的連番發(fā)問,感到驚訝的反而是吉田。
“你們的問題,我有的答不出來。”吉田不明白,為什么比起污泥處理技術和工廠外觀,這群中國人更關心在他看來理所當然的問題:“你們建設、運營的錢從哪里來”“你們廠是事業(yè)單位還是國有企業(yè)”“你們和政府關系怎么樣”“不同的政府主管部門會不會打架”……
吉田不知道,這些問題正是中國污泥處理與處置困境的癥結所在。
污泥是污水處理過程中形成的沉淀物,富含大量有毒有害物質(zhì)及重金屬。中國水處理產(chǎn)業(yè)長期“重水輕泥”,住建部城建司水務處處長曹燕曾表示,截至2014年底,中國近50%的城市污泥未做到無害化處理。
中日差距二十年
就在研修團赴日的一周前,住建部城市建設司巡視員張悅宣布,環(huán)保部和住建部即將聯(lián)合發(fā)布通知,將污泥處理處置與減排核查正式捆綁,一旦無法核實污水處理廠污泥去向,將扣減污染物減排量。
“文件下來以后,大家會有一定壓力,但是壓力不是直接給各位污水處理廠廠長的,是給城市政府。”張悅在一個污泥處理處置的研討會上表示,政策通過把污水處理廠的污泥納入總量減排核算,責任落實到地方政府,以此推動污泥的無害化和減量化。
“污泥難題不是一天兩天了。”張悅感慨,“我們爭取把它作為一個重點工作,在十三五期間解決了。”
北京市市政工程設計研究總院副總工程師杭世珺至少已為此奔走呼吁了二十年。而中日在污泥處理上的差距,也“至少二十年”。
杭世珺在1980年代留學日本,研修城市污水處理。“那時候,日本的(污泥)焚燒爐都建得滿滿的了。”2016年4月14日,杭世珺回憶。
日本最早的污泥處置方式是海洋投棄。在1920年代,日本第一座污水處理廠運行過程中產(chǎn)生的污泥,就直接傾倒入海。
其后,日本污泥處理經(jīng)歷了自然干燥、脫水填埋等一系列演變。到1960年代,因為征地困難,日本開始推進能快速實現(xiàn)污泥減量化的焚燒技術。1977年成立了污泥處理調(diào)查委員會,強調(diào)污泥的資源化和再利用。1996年,日本修改下水道法,要求公共下水道管理者用脫水、燃燒等方式實現(xiàn)污泥減量的同時,應當盡量將污泥作為燃料或肥料實現(xiàn)再生利用。
據(jù)東京大學水環(huán)境控制研究室教授、日本下水道協(xié)會成員古米弘明介紹,近十年來,日本污泥年產(chǎn)生量變化不大。2010年,日本全國產(chǎn)業(yè)廢棄物總量約3.86億噸,含水率97%的污泥占約19%,約7471萬噸。
雖有污泥熔融、碳化等新技術出現(xiàn),但焚燒依然在日本占據(jù)主流。2008年,日本干污泥(經(jīng)過脫水等處理后的污泥)年產(chǎn)量220萬噸,其中焚燒灰渣占68%。
在進行減量處理的同時,日本很注重污泥的再生利用。
日本2014年度下水道新技術研究所年報顯示,污泥有效利用率從1988年的15%,已提高到2010年的78%,2011年37%的污泥用于制作建筑材料。
“污泥處理在中國的演變過程跟日本很相似,但中日的差距主要不是技術。”杭世珺表示。
中節(jié)能博實(湖北)環(huán)境工程技術股份有限公司總經(jīng)理錢鳴亦有類似觀點,該公司2008年引進日本的污泥碳化技術。“日本下水道協(xié)會把碳化作為替代熔融和焚燒的技術,是比較先進的。我們在引進時也根據(jù)中國污泥狀況做了改進。技術不是問題。”錢鳴謹慎地說,“但是,在推廣過程中還是有一些障礙、一些困惑。”
“我們完全沒考慮要掙錢”
錢鳴遇見的障礙,首先就是污泥處理處置的費用不足。
“國家在技術政策中明確指出,污泥(處理處置)的費用在污水處理費中代收,但代收多少沒有明確界定。既然不明確,政府也就不論技術好壞,反正哪個方法便宜,就先用哪個對付一下。”錢鳴指出,“很多運營污水處理的公司喊窮,現(xiàn)在污水處理費都不夠,還拿多少給污泥呢?”
“我們運行靠的也是居民的污水處理費。”在舞洲污泥處理中心,相關媒體將錢鳴的困惑轉(zhuǎn)告吉田,得到這樣的回答,“我們完全沒有考慮要掙錢。我們收的(家庭月用水量)10立方米以內(nèi)550日元(不含稅,約33.6元人民幣)就是根據(jù)運營成本核算好的,再向居民收取。”
舞洲污泥處理中心的建設費用為620億日元,其中六成來自日本國家政府,四成來自大阪政府。建成以后,其日常運營費用不再依靠國家補貼。
在日本,居民需按月用水量交納水道費和下水道費,后者相當于中國居民水價中的污水處理費。大阪市水道局網(wǎng)站顯示,當家庭月用水量在10立方米以內(nèi)時,水道費為1026日元,下水道費為594日元(含稅)。在10至20立方米之間,下水道費為66日元/噸(約合人民幣4.04元)。
“大阪的污水處理費在日本各大城市中是最低的。”吉田強調(diào)了兩次。但這個數(shù)字已足夠讓他的中國同行羨慕——中國一家產(chǎn)業(yè)研究機構的水價數(shù)據(jù)庫顯示,目前全國36個省會城市及計劃單列市的污水處理費平均為0.82元/噸。
和中國一樣,日本的污泥處理費被包含在污水處理費中。日本國土交通省數(shù)據(jù)顯示,2012年日本下水道維持管理費共9008億日元,污泥處理費占5%,即450.4億日元(約27.52億元人民幣)。
“中國排水費(即污水處理費)就這么一點,污泥處理費高了就吃不消。排水費要提高,自來水費就得上去,那就要開聽證會,老百姓又可能不理解你。”上海交通大學固體廢棄物處理處置技術研究所所長朱南文透露,上海一座污水處理廠和某水泥集團談一個污泥建材化利用項目,談了七八年也沒開建,“就是價格談不來”。
朱南文研究過大阪市對污泥建材化利用項目的支持機制。大野污水污泥處理廠(除了舞洲,大阪另外一個污泥處理工廠)用污泥焚燒灰制造透水性磚,政府除了按照污泥填埋的同等價格進行補貼外,還會優(yōu)先購買用于市政建設,保證銷路。“日本的整套體系都設計好了,不會卡在哪個環(huán)節(jié)。”朱南文說。
“日本污泥處理是不惜代價,他們的工程建設成本和運行費用其實比我們高多了。”錢鳴表示。
而在中國,污泥處理處置費用該誰出,還是一筆糊涂賬。張悅的意見或許代表了目前的政策思路:“(污泥)無害化治理,政府應該承擔成本。”
“體制差別,沒法借鑒”
“原來,吉田是公務員啊!”就舞洲污泥處理中心的性質(zhì)糾纏了將近二十分鐘以后,研修團終于搞清楚了吉田的身份。
舞洲污泥處理中心隸屬于大阪市建設局下水道部,但負責運營的是一個共同企業(yè)體。目前的工作人員共有85人,其中9人是大阪市建設局的公務員,包括吉田在內(nèi)。
吉田聽不懂國有企業(yè)和事業(yè)單位的區(qū)別,而污泥處理廠和政府的關系問題,對他而言也過于微妙。他只能一遍又一遍地解釋:“我們是屬于大阪市的,但為了更好地運營,有專門的運營單位。”
在中國,作為第一個將污泥碳化技術投入商業(yè)化運營的企業(yè)負責人,錢鳴不僅要處理和政府的關系,還要處理和政府不同部門之間的關系。
“日本的污泥處理,協(xié)同性做得好。比如將污泥和餐廚垃圾協(xié)同進行厭氧處理,咱們國內(nèi)也有幾個項目,但在實際操作中總有些瓶頸突破不了。垃圾屬于城管部門的,市政污泥屬于水務部門,污水處理廠建設屬于住建部,監(jiān)管又歸環(huán)保部,不在一個體系里面,怎么協(xié)同?”
有一次,錢鳴在日本秋田市參觀了幾個固廢處理中心。在其中一個推行污泥與餐廚垃圾焚燒協(xié)同發(fā)電的處理中心,他很感慨:“你知道這個中心的主任是誰嗎?就是秋田市的市長!市長是處理中心的一把手,下面的管理體制就比較簡單了。”
在杭世珺看來,目前中國污泥處理處置最嚴峻的問題,不是缺少經(jīng)濟杠桿。“這不是我一個專家的意見,大家都認為后門堵死了。”
管理上政出多門。例如目前我國建設部門在污泥處置上鼓勵土地利用。“問題是,農(nóng)業(yè)部不讓污泥進土地。建設部門有擬定標準,但農(nóng)業(yè)部不認。東北一個污泥堆肥廠做得很好,但沒出路。”杭世珺研究了一輩子污水和污泥,參與了許多標準制定,她將中國污泥處理的癥結歸為政府部門間的阻力太大。
赴日研修團中有一位媒體人。在參觀舞洲污泥處理中心之前,他想寫一篇文章介紹日本的污泥處理處置經(jīng)驗。但參觀結束后,他放棄了這個念頭:“體制差別太大,沒法借鑒。”